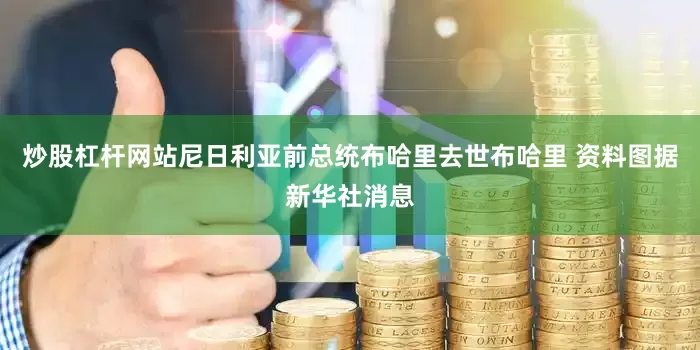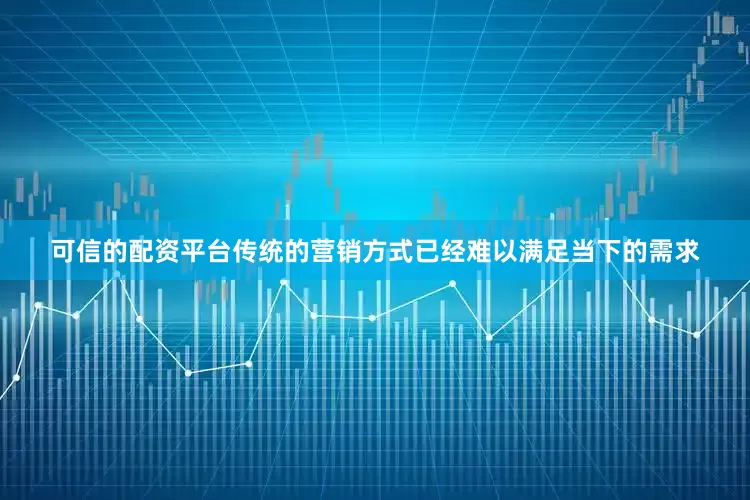冯国璋祖父,字华甫,诞生于1859年1月7日,即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四日。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怀仁堂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遗憾的是,1919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岁。
去年(2009年),恰逢祖父仙逝九十周年纪念。自2007年起,河北省河间市委、市政府便着手对祖父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故里西诗经村国葬墓进行了部分修复与重建。2009年,一场隆重的公祭活动在此举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文史领域亦焕发出新的生机。研究历史人物与问题,我们秉持客观立场,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一背景激发了我们记录祖父生平事迹的愿望。通过追溯家中长辈的口述,不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必要的澄清、校正和补充,也让世人得以对祖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及其人格特质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刚范先生,笔名公孙訇,曾对祖父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撰写了《冯国璋年谱》一书(以下简称《年谱》)。刘刚范研究员曾向我们阐述道:“冯老先生一生功勋卓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我国现代军事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其次,在民国建立之后,他坚定维护共和体制,坚决反对帝制,包括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的坚决抵制,堪称维护共和的重要功臣;最后,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坚决反对段祺瑞发动内战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积极倡导通过和平途径实现国家的统一。”刘先生的这番评价,既贴切又中肯,深刻地揭示了祖父的卓越贡献。
01.家境贫寒,辍学参军。
祖父于1871年至1875年间,于家乡河间的毛公书院潜心苦读,毕业之际,其优异的考试成绩位列榜单之巅。1881年,他踏入保定莲池学院的校门,但翌年因家境凋敝,被迫中断学业。1884年,祖父选择放下书卷,投笔从戎,前往天津大沽口。我们的父亲曾这样向我们讲述祖父幼年时家道与经历:“爷爷自幼便热爱读书,在毛公书院求学期间,成绩斐然。然而,因家贫无力继续深造,无奈之下,他投身军旅,起初只是担任了一名炊事兵。”在军旅生涯中,凭借吃苦耐劳的品格与自身的文化素养,祖父得以被推选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深造。在学堂假期,他返回河间参与乡试,成功考取了秀才。此后,他重返武备学堂,继续攻读步兵专业,1890年,凭借优异的毕业成绩,祖父被学堂留任,成为了一名教员。
父亲言道:“爷爷对聂军门(聂士成将军)极为敬仰,遂投身其麾下。聂将军以战功显赫,荣获清朝赐予的‘巴图鲁’称号。爷爷恪尽职守,深得聂军门赏识。”在此期间,祖父被誉为“武校文生”,曾随聂将军多次赴东北三省边境考察,协助绘制地图及撰写注解。祖父勤勉尽责,协助聂将军编纂《东游纪程》,使清军对辽东地区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为聂将军日后在东北地区指挥抗敌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祖父亦深受聂将军的器重。
02.朝鲜战败 小马渡江
1894年6月,祖父随聂将军奔赴朝鲜,抵御日军。然而,那时的清政府并未洞察到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意图——是为侵略中国做铺垫。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装备落后、兵力悬殊,加之清军统帅叶志超的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冲锋在前,祖父亦英勇善战,但在装备精良的日军猛烈攻势下,淮军未能有效抵抗,聂将军只得率领祖父和士兵们节节败退。这场战争,可谓是一场边战边逃、边逃边战的惨烈之战。
《年谱》中记载,彼时冯国璋及其护卫阎升,仅凭一骑骏马,勇猛地强行渡过了江河。
“马通人性,有一日,负责照料小马的人前来告知三爹(即我们的三伯父冯家遇,字叔安),小马食欲不振,似乎生病了。三爹立刻前去看望,轻拍马背,说道:‘这老东西,还没死呐。’稍作停留后便离开。然而,三爹刚进屋,照料马的人又来报告:‘小马躺下了,吃什么都不吃。’三爹立即回应:‘知道了。’随即匆忙赶到马棚,蹲在地上轻拍小马,说道:‘老家伙,你怎的听不懂玩笑话呢?我刚才跟你讲笑话呢。’说着,他亲自用手将精饲料与青草混合,为小马喂食。小马吃了几口后,突然站立起来。三爹又安慰了几句,小马这才逐渐好转。”
父亲续道:“他们二人跋涉过河,疲惫不堪,饥渴交加,终于抵达山脚,偶遇一位小和尚。他们向小和尚求助,寻求水源与斋饭。小和尚在询问了他们的姓氏后,说道:‘施主请随我上山,我家师父命我在此恭候您。’二人心中充满感激与疑惑,便随小和尚一同上山,并在庙中安顿下来。老和尚与爷爷交谈之际,他透露:‘你日后必成大器,日后若有需我相助之处,我自会登门拜访……’在庙中休憩数日,向老和尚道别后,爷爷便重返聂军门的麾下。”——此事应发生在1895年10月。
‘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你来此一趟不易,但此乃你们寺之镇宝,我难以全数收下。我愿代你保管四个玉碗,玉瓶则请带回去。日后自当还有相见之时。’老僧人在此逗留数日,携玉瓶离去,此后便再无音讯。”父亲推测,老僧人所言东北之大难,或许是指日军密谋发动侵华战争之事。他说,那四个玉碗一直由我们的大姑(冯家逊)保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姑遭受迫害,无奈之下,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四个玉碗自此便下落不明。
依照先辈的讲述,在清朝末年,祖父投身聂士成将军麾下,与聂将军并肩守卫摩天岭长达三个月。那期间,祖父曾与聂将军携手,在一场激战中击败了日军。父亲曾回忆道:“尽管甲午战争以我国的败北告终,但爷爷曾随聂将军,以誓死一战的决心,率领部下将日军围困,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在摩天岭,聂将军所部面对孤立无援的困境,依然英勇抗敌。祖父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知识,向聂将军献策,于各处竖立清军旗帜,布下看似人马众多的疑阵,以此迷惑日军。同时,他在要害之处部署重兵,巧妙运用了兵法中的“虚实相间”、“声东击西”之术。最终,在援军的协助下,成功击败了敌军。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这是唯一一支击败日军的队伍。因此,聂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而祖父亦功勋卓著。经过甲午一役,祖父已然成为聂将军的得力干将。
当时,对日作战的败局已无法扭转。随着辽东半岛的沦陷,清政府不得不签署了那一份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1月末,祖父随聂将军驻防山海关。在此期间,祖父因在对抗日军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功勋卓著,已被从五品官职晋升为聂军军械局的督办。
“裕庚,乃祖父在武备学堂的恩师,对其极为赏识。在日期间,祖父得以拓宽视野,结识了多位日本军事界的杰出人才,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宝贵的知识。同时,他还对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训练方法和理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归国后,祖父整理研究成果,出版了好几部兵书。”
“爷爷对裕庚言:‘现今已是洋枪洋炮盛行之世,大刀长矛如何能敌?正是因此,甲午一役才致败局。我认为我国必须改编军队,全面革新,否则将难免灭亡之祸……’裕庚深以为然,并表示朝廷中也已有同他观点之人。”不久,清政府再次派遣祖父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赴日进行军事考察。经过这两次深入的考察,祖父在军事科学领域的认知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在赴日本进行考察之后,我所撰写的兵法著作,曾惠赠予聂将军以及荫昌先生(字午楼,彼时担任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先生不仅是祖父的恩师,更对他卓越的才干以及所创作的数本兵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03.辅佐袁氏,训练新军。
1896年岁末,清政府决定委派袁世凯至小站指挥新军训练。祖父在武备学堂的旧友,如王士珍、段祺瑞等,均已抵达小站,这不禁令祖父心动,却也让他陷入矛盾。祖父固然渴望加入新军训练,然而,聂将军对他的知遇之恩难以割舍,尽管聂将军对编练新军的道理洞若观火,祖父仍不忍心提出离职的请求。我父亲曾提及:“最终是荫昌大人举荐,袁世凯多次恳请聂将军放行,聂将军才将祖父送至小站。离别之际,二人泪眼相望,依依不舍。”
抵达小站后,袁世凯以亲切有礼的态度接待了祖父。据记载,袁世凯将祖父所携的数册兵书视为无上珍宝,称之为“鸿宝”,并赞誉“学界之子无人能出其右”。祖父与袁世凯同年出生,且比袁世凯年长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素来擅长礼遇贤能之士,不久便将祖父尊称为“四哥”,并将新军操练、营务等要事全权委托予祖父及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同仁。祖父在小站勤奋耕耘,与王士珍、段祺瑞共同编纂了23册全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训练新军的核心教材。在袁世凯的麾下,三人共谱华章,其成就甚至得到了德国教练的赞赏。后来,这三人被誉为“北洋三杰”。
父亲回忆道:“在那个小站,爷爷可谓是提振了国人的士气。那时,我们聘请了几位德国军官担任教练,那些德国人傲慢无礼,对中国军官颇为轻视。每当他们有所不妥,爷爷都会据理力争,甚至不惜与他们对峙。尽管如此,德国军官试图动手,却被爷爷的士兵制止。最终,他还将爷爷告上了朝廷,但终究还是不得不将他驱逐出境。”
史料中对此事有着详实的记载:当时,小站练兵特聘数位外籍教官,其中一位德国人名叫曼德,他傲慢无礼,早已被清朝官员所纵容。一次,曼德酒后迟起,延误了既定的训练安排。祖父与士兵们在寒风中于操场久候,而他迟迟未至。祖父只得亲自寻他,他却不仅不道歉,反而粗鲁地欲行凶,幸被士兵制服,并未对其造成伤害。然而,他反而反咬一口,借助德国公使向朝廷诬告祖父。袁世凯当时亦颇感忧虑,但祖父提议邀请英国记者揭露真相,舆论顿时哗然,朝廷遂下定决心明确外国教练的职责,并果断解除了与曼德的合约,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过后,袁世凯声望大增,对祖父也更加倚重。
小站练兵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引领了我国军事现代化的征程,更孕育了一大批军事英才和政治领袖。在民国初期,众多总统、总理、总长以及众多军事将领均出自小站练兵的摇篮,从而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强大“北洋系”。
“祖父于北洋各学堂所培育之才,多达数千人。现今无论上至统帅,下至校尉,以及内部部曹、外部幕职,凡北洋出身的,要么是同窗,要么是其门生。”
自小站练兵起,袁世凯声望日隆,我祖父亦随之官职迭升,先后执掌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督办、练兵处军学司正使、保定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督办以及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等显赫职位,同时亦多次获得清廷的嘉许与表彰。
袁世凯对祖父的赏识、提携与重用,祖父曾多次表达出自心底的“受恩深重”。无论在清朝末年或是民国初创,袁世凯始终对祖父深信不疑,诸多要事均仰赖祖父之力得以圆满完成。
父亲曾如此述说:“你祖父执掌贵胄学堂之职,彼时求学之士皆为蒙古与满清之贵族。学堂之中,更设有‘王公讲习所’,定期授课之处,王公大臣无不悉数光临,涛七爷(载涛,乃溥仪叔父、摄政王载沣之弟)亦曾亲临听讲。然有八旗子弟懒惰成性,怠于学业,他人皆畏而避之,唯独你祖父不畏艰辛,执鞭驱策,以示严教。”此一往事,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股票配资十倍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